
在城市“卷”够了,要不要去农村试试?这两年,去上海郊区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。沪郊本地人,在市区工作,节假日回村看望父母,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村口田间开起了咖啡馆和花店,甚至还有窑烤面包——完全打破了对乡村的刻板印象。
有人戏称,“北漂沪漂,不如来江浙沪的农村做村漂”。
可真别说这是一句玩笑话,与其他地方的“村漂”不同,上海的“村漂”自带一种时髦气质。青浦、松江、崇明、金山等地,不仅保留着乡村的生态,更处于上海大都市的辐射圈内——多数村庄距离市区仅需要1到2小时车程,超过3000万城市人口催生的“微度假”需求,为上海的郊区带来了接近一线城市审美的消费活力。
随着“村漂”创业的热度攀升,大家对于他们的认知却呈现两极。有人视为“人生新赛道”,也有人认为是城市受挫后的逃离。现实究竟如何?在乡村创业,到底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新出路,还是被动逃避的退路?
都市来客,找寻新可能
在许多人的想象中,去乡村开店等同于告别内卷、拥抱慢生活,是一条逃离城市压力的退路。然而当真正走进上海郊区,与店主们深入交流,你会发现这些“村漂”非但没有躺平,反而进入了一种比城市更全方位的“自卷”状态——从产品研发、社群运营到品牌建设,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方位涉猎,容不得半点懈怠。
采访过程中,几个真实创业故事,或许能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“村漂”的奋斗状态。
设计师王守伟最初来到青浦和睦村时,只想将老宅作为设计概念的展示地,却意外发现乡村市场的巨大潜力。在这条仅有300米长的水街上,游客不仅消费咖啡,对高品质住宿、特色餐饮的需求同样旺盛。在政策扶持下,他的创业版图在两年内迅速扩张,市场的倒逼让他从“小试牛刀”转向了“商业深耕”。到现在,他已经流转了村内八间老宅,推出三家定位各异的小院,盈利可观。
 赵巷镇和睦村,王守伟已经流转了村内八间老宅,推出三家定位各异的小院。
赵巷镇和睦村,王守伟已经流转了村内八间老宅,推出三家定位各异的小院。
在奉贤的李窑村,一家面馆的店主原本只想“开个小店,够吃够用”,结果开业首日的上午,准备的50份食材就全部售罄。不断有客人询问“明天还开吗”,让他迅速打消“慢生活”念头,转而钻研新品、优化流程,还建起社群做特色推广——“乡村市场很实在,你不用心,人家下次就不来了。”
不仅如此,一些“村漂”还想将城市的潮流业态带到农村。在嘉北郊野公园,“沸舍”的店主虾米正在做出一些尝试,她考虑引入乡村疗愈相关的业态——像瑜伽、颂钵等。在一片稻田里做疗愈,她坚信“这在乡村会非常有市场”。
在这些“村漂”极为相似的创业叙事里,不少人最初都是带着“退路派”的心态,希望通过乡村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型。
但退路的幻想,在开张营业的那一刻便已破灭。市场的真实反馈让他们清醒认识到,仅靠情怀支撑的“躺平模式”难以长久。只要开了店、做了生意,就必须遵循商业逻辑,用心经营。
上海郊区,成为理想试验场
在业内,九月被称为“丰收的月份”,也是“村漂”们的旺季。天气开始转凉,随着稻田转黄、鲜花盛开,骑行和露营的人变多,“村漂”们熬过了淡季,开始准备迎接一年中的热闹时段。
最近,店主吴慧颖正在升级自己的咖啡馆。这是一家名为“一杯乐”的小店,坐落在距离乐高乐园10公里的枫泾古镇内。如果不是熟客,很难找到这家“躲”在弄堂里的咖啡馆。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装修,咖啡店后的“主题民宿”将在九月底正式开始营业。
 “一杯乐”咖啡的花墙成为不少顾客的打卡处。
“一杯乐”咖啡的花墙成为不少顾客的打卡处。
但也不由让人担心,这里离乐高乐园那么远,会有人愿意来这家民宿居住吗?
吴慧颖却毫不忧虑,“上海的消费者们都是很聪明的,他们会愿意为品质和服务质量买单”。开店三年,她凭借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审美已经吸引了一批忠实顾客,连工作日都座无虚席。这家店在社交媒体上也有极高热度,“有从市区来的,甚至有从宝山、嘉定来的”,复购率极高。
细细想来,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并不令人意外。围绕这座超大城市,郊区为“村漂”群体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创业试验场——它的“高潜力”既保留了乡村的自然生态与开阔空间,又承接了城市的消费人流与购买力,特别适合小微业态在这里试水成长。
市场优势是首要支撑。城里人的“微度假”需求,为郊区业态带来了稳定而庞大的客源。如奉贤的无忧闲院,去年借助稻田景观实现单日数万元的营业额;又如青浦的“前院后院”民宿,能够吸引市区顾客专程驱车前来品尝打边炉;还有宝山的枋园鲜花农场,独特的设计感吸引了不少美学同好,一座难求……
与此同时,社交媒体平台的高传播效率,进一步放大了郊区创业的曝光效应。像李窑村这样的村庄,凭借几张照片就能迅速走红,这种天然的流量优势,是很多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。
什么样的业态能在乡村真正扎根?
自2021年上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以来,郊区整体风貌、道路交通与网络设施明显提升。基础设施的持续升级,为乡村创业扫清了最大障碍——如今创业者不再受限于硬件短板,得以真正专注于商业模式和产品本身的创新。
但这片热土并非对所有业态“一视同仁”。
记者走访多家乡村店铺后发现,咖啡馆和农家乐几乎是很多人首选的创业方向,却也同样成为最快退场的领域。尤其是农家乐,看似门槛低,实则挑战极大:供应链整合难、口味众口难调、服务缺乏专业性……每一条都足以让一家新店迅速沉寂。
李窑村走红之后,当地的“村漂”代表屠华斌就成了不少新创业者的咨询对象。他坦言,自己一边分享经验,一边也劝退了不少盲目跟风、不符合乡村实际需求的业态。
“咖啡馆和农家乐算得上是‘重灾区’”,屠华斌直言,“它们的生命周期往往非常短暂。”尤其在夏季淡季到来时,即便上一年还人气火爆,今年也可能迅速被市场淘汰——高度同质化的业态终将经历大浪淘沙。
而真正能活下来、走得远的项目,往往掌握一个核心原则:不是乡村需要咖啡店,而是咖啡店需要借力乡村的独特场景和价值。
这些成功的“村漂”创业者不仅在商业上获得成功,更在潜移默化中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他们将城市里的潮流业态带到农村,同时巧妙地将农村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商业体验中,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新经济——
有的巧妙嫁接本地物产,如“崧泽咖啡”链接“上海第一稻”历史,推出米乳拿铁;有的重构空间功能,如把村口的养老院改造成乡村公共客厅的“由心·徽饮”;还有的主动与村民共生合作,如浦东的“朱雀小院”邀请本地厨娘掌勺,并将部分利润反哺村集体……
从这个角度看,这些店不再把乡村当作背景板,而是真正成长为乡土的一部分。
在地共生,将“慢节奏”转化为“吸引力”
采访中,一个新的问题也在不断生长:“村漂们”来到村庄,他们又能为这片土地带来些什么?
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“连接”这个词。在宝山区一家开业两年的店铺,初期店主还曾困惑于如何与村民顺畅打交道,可没过多久,她便发现自己的经验与乡村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在“村漂”眼中,老农具、土灶台不再被视作“过时”的象征。在“村漂”到来之后,这些传统元素逐渐融入现代消费场景,旧物件成为店铺里的摆设,土灶能做出吸引游客的农家菜。连本地村民也开始意识到:“原来我们村里的这些东西,也可以这么有意思。”

这种“连接”远不止于“旧物新用”,更在于打通壁垒。农村缺什么、需要什么,“村漂”常常从城市引入资源,用设计理念、营销渠道去填补农村发展的空白;也能精准捕捉城市消费者对“原生态”“慢生活”的渴望,把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转化为可体验的产品。这种连接不再是单向的“帮扶”,而逐渐演变为双向的互动。
不少“村漂”还主动打破“外来者”的边界,邀请村民深度参与经营。忙季时,有人雇佣村民协助收割水稻、打理田园,为他们增加家门口的务工机会;也有人聘请村民担任“民宿管家”,由他们带领游客体验播种、采摘等农活——毕竟,村民最熟悉本村的风土人情,他们的加入不仅让游客的乡村体验更真实鲜活,也让村民从“旁观者”变成了“参与者”。
传统的技艺与空间也在合作中被重新激活。在青浦和睦村,民宿特意保留了老宅的木梁、土灶和旧农具。在新建村,时不时请村民来教做塌饼、包粽子,前段时间还引入了现榨菜籽油,既丰富了游客体验,也为店铺带来额外收入。
正是这些看似微小却持续不断的尝试,让乡村的价值不再局限于“提供农产品”,更慢慢成长为输出体验、内容与情感的新空间。一批如稻田婚礼、企业团建、农事研学、定制民宿的新业态持续生长,乡村独有的慢节奏、原生态与老传统,也正转化为打动城市人的吸引力。
当记者再次抛出这个问题,询问“进村是不是逃离城市的退路”时,大多数“村漂”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有创业者说:“在乡村创业其实更‘卷’,你要懂商业、懂乡村、会做产品、还要和村民打交道,光想躺平,肯定做不下去。”
从这个视角看,“村漂”从来不是退路,而是一条需要深耕的新出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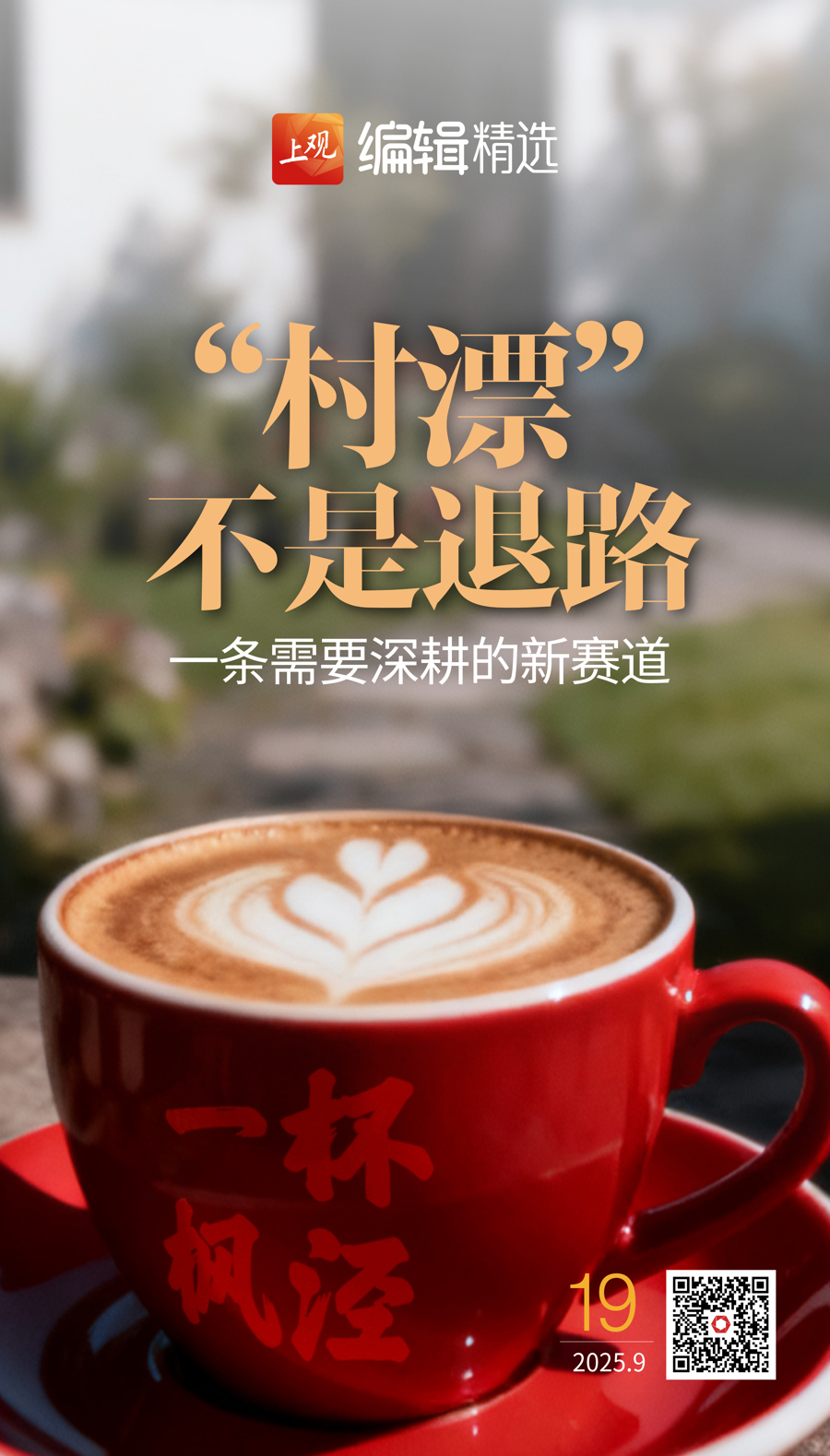 海报设计:邵竞
海报设计:邵竞
658金融网配资-配资查询网站-股票加杠杆网站-配资机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